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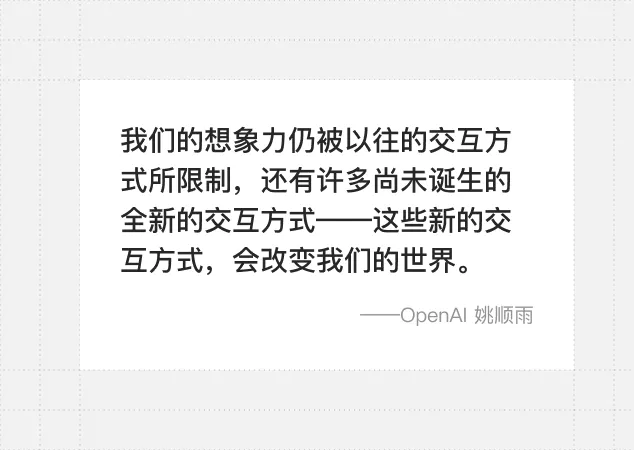
2025年4月,OpenAI研究员姚顺雨发布了一篇有名的博文《The Second Half》,宣告AI主线程的游戏已进入下半场。这之后,我们与他进行了一场播客对谈。
姚顺雨毕业于清华和普林斯顿大学,博士期间意识到语言是人类发明的最重要的工具,也是最有可能构建通用系统的,于是转向Language Agent研究,至今已6年。
这场对谈有两位主持人,分别是我和李广密。姚顺雨表达了许多此前从未分享过的观点。比如:
我们的谈话从个体出发,共同探索由人、组织、AI、人与机器的交互,所抵达的这个世界智能的边界以及人类与机器的全景。
此前,我们关于Manus肖宏、Youware明超平、Lovart陈冕的访谈,记录了华人Agent创业者在应用上的探索。而姚顺雨的访谈,描绘的则是另一面:他在硅谷最前沿的AI实验室做Agent研究,他如何看待这波浪潮、模型与应用的边界,以及那些Agent逐浪者呢?
这是「语言即世界工作室」(Language is World Studio)成立后发布的第三篇长文访谈,姚顺雨很意外地从另一个角度帮我回答了,我们工作室创立的初心。
为什么我们相信语言是这个世界的本质奥秘?
他的表达是:“语言是人为了实现泛化而发明出来的工具,这一点比其他东西更本质。”
不得不说,姚顺雨的通篇表达有一种技术之美感,我个人十分喜欢。
以下是对姚顺雨的访谈节选(作者进行了语言优化。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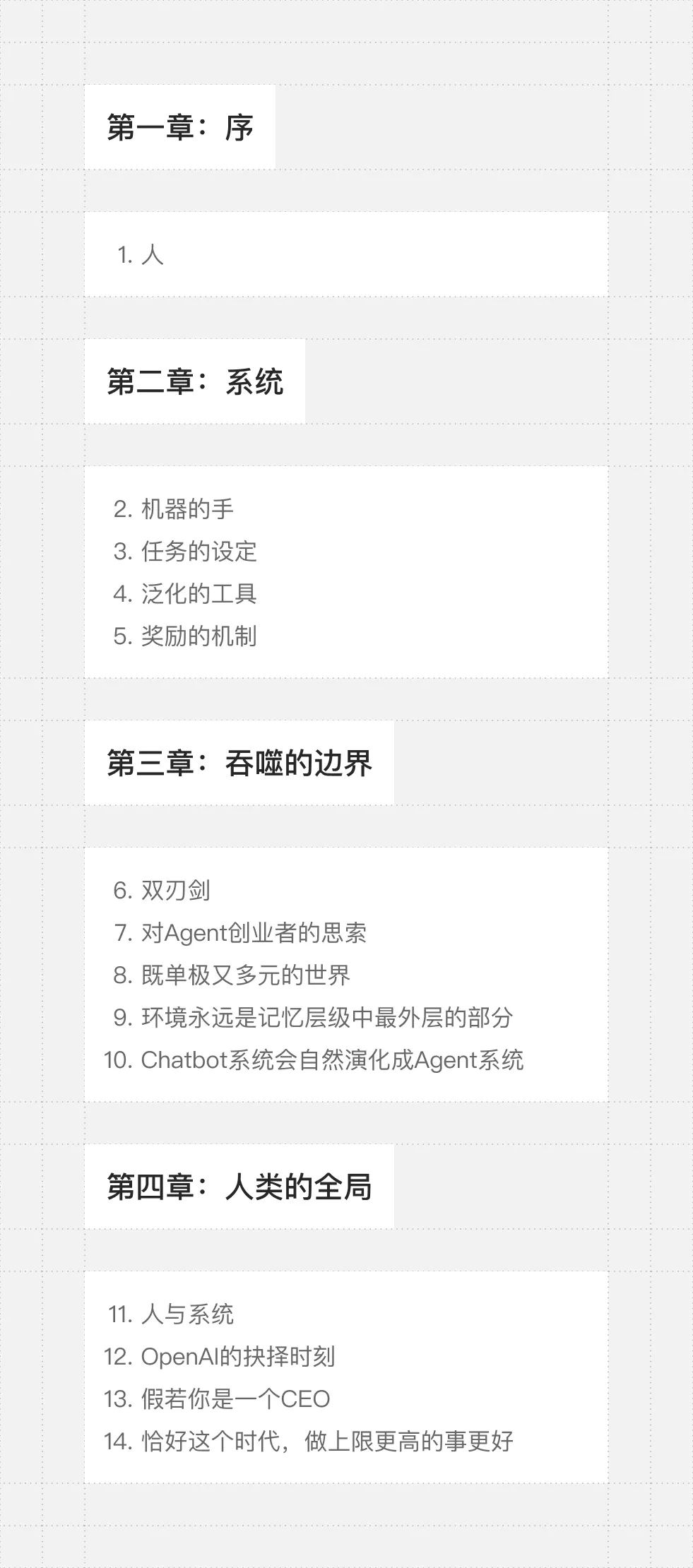
第一章 序
01 人
“我一直有这个非共识,
我想要去做Agent”
张小珺:我们今天的嘉宾是OpenAI姚顺雨,他的研究方向是Agent。前段时间顺雨写了一篇有名的博文《The Second Half》,告诉大家AI游戏已进入下半场。
这次节目我们第一次尝试有两位主持人,除了我还有大家熟悉的广密。
顺雨,我看了你的资料和你写的文字,从你的语言里读到一种反叛精神,我对你这个人很感兴趣。你能不能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,聊聊你的经历?
姚顺雨:你说反叛精神?这很有意思。
我感觉我是个非常乖的学生。从小到大就是按部就班的学习。
本科从合肥考到清华,读姚班。在姚班大家会告诉你去美国读PhD,我就去美国读PhD,我在普林斯顿读PhD。读PhD之后很自然,OpenAI是做research(研究)最好的地方,就加入OpenAI——感觉我前28年的人生,非常的乖。
张小珺:你是15-19年在清华姚班,19-24年在Princeton,24年毕业进OpenAI。你在本科学的不是AI,是怎么进入AI领域,继而又进入Agent领域?
姚顺雨:姚班的传统偏理论计算机科学,但我可能有一点反叛精神吧。
当时,我觉得很多重要理论问题已经解决得差不多,比如将某个图算法的复杂度从n的2.83次方优化到n的2.82次方,这种改进在现实中意义不大。
我在2016年上李建老师的一门课,看到一个multi-modal embedding(多模态嵌入)的demo,展示了embedding(向量表示/嵌入)一个非常神奇的例子:比如用“king”的embedding减去“man”,再加上“queen”,结果接近“woman”的embedding——这让我第一次意识到,深度学习在语义表示上居然能做到这么惊艳的计算。
当时清华,尤其姚班,在Deep Learning(深度学习)的老师和资源还比较有限。2018年,我按照姚班传统去海外交流,去了MIT,师从吴佳俊学长,我才真正系统性开始做Deep Learning。
最初我做的是Computer Vision(计算机视觉),但渐渐意识到Vision很难实现通用人工智能。我的直觉告诉我:Language是一个更核心、更有潜力的方向,于是读博后转向语言模型研究。
张小珺:你是怎么进入Agent方向的?
姚顺雨:也算是某种机缘巧合吧。我的导师之前做过一些研究,探讨怎么在一个简单的语言游戏环境中训练智能体(Agent)。大概2016或2017年的工作。
那个项目是用一个基础RNN模型,在一个很小规模的文字游戏里,训练模型进行一些简单动态交互。比如,模型可以学会,“过桥之后就可以到河对岸”——这样简单的常识或逻辑推理。
我读博,本来是被计算机视觉(Computer Vision)录取,但我已经不太想做视觉了,主动去找语言(NLP)老师聊。
我遇到现在的导师KarthikNarasimhan(普林斯顿计算机科学副教授),开始一起头脑风暴项目点子。我当时说:现在的语言模型,比如GPT-2,已经比你们当年用的模型强太多,它们玩游戏是不是表现也会更好?
他说,maybe that' s a good idea。我们就开始做了。
从那以后,我就一直做智能体相关工作,到现在6年了。
张小珺:Agent或Language最吸引你的是什么?
姚顺雨:是它的可泛化性(generalizable)。绝大多数事,你都可以用语言表达。
我当时隐隐约约有个直觉:你如果真想去实现AGI(通用人工智能)——那时还没人提“AGI”这个词——但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个非常通用的系统(general system),你就得去构建一个智能体。
回头看AI历史,很久很久以前,从Herbert Simon(赫伯特·西蒙)在1960年代开始,大家最早的想法就是要做一个Agent。当时大家的野心很大——想用一个夏天搞定视觉,再用另一个夏天搞定语言,拼在一起,去做一个Agent,他就应该比人还聪明。
但这事太难了。慢慢地,AI变得非常碎片化。大家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小。比如,有的人研究视觉一小部分问题,有的人研究语言某个子任务,越来越细分,越来越垂直。
但到2015年之后,开始出现Scaling Law(扩展规律),包括很多研究突破,历史上一些关键时刻也在提示我们:也许我们应该从这种“垂直式思维(vertical thinking)”重新回到更“通用式思维(general thinking)”,再去尝试构建真正通用的系统。
张小珺:当你进入Agent系统做研究,要让语言模型真正行动起来,你意识到最重要的几件事是什么?
姚顺雨:第一年最大收获是:要用GPT,不要用BERT。
可能现在很多人不知道BERT,当时语言领域最火的模型叫BERT。想法是:我有一句话,通过某种方式学到这句话的一个表示,通过这个表示做很多下游任务,比如做一些单选题,或者基于选择的任务。
当时95%的人做BERT,只有5%的人做GPT。这也是因为当时NLP的主要任务都是一些:我有一句话,这句话是积极的还是不积极的;我很讨厌这个电影,这是一个负面的句子。都是非常简单的事。这种事BERT确实效果更好。
但你会发现,如果你要做一个language Agent,你需要的不只是选择能力,而是去自由产生新动作的能力。
当然如果你在玩围棋,或者视频游戏,选择有限。如果你玩马里奥兄弟,他就是上、下、左、右。但如果你玩基于语言的游戏,动作是自由的。比如我在这个游戏可以用剑杀怪兽,或者我可以去第三个房间,或者我可以用金色钥匙打开第一个房间的门。BERT永远做不到。
世界的本质就是,你的行为空间是open-ended(开放)的,这种在开放空间决策的能力BERT永远做不到。我发现这个之后,就再也没用过BERT。
第二个learning是:任务或环境非常重要。
当你有一个非常差的任务,你永远不可能学到非常好的东西。当时有很多人在做:这个句子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?a这句话能不能导致b这句话成立?当时这些任务看上去很难,现在看非常简单。
首先你要找一个足够有挑战的任务,这个任务能做出本质的新方法。当时你想去做Agent或语言Agent,实际上没什么选择,只能去做文字游戏。
Zork是个非常经典的文字游戏。你在一个基于文字的世界里,有点像一个互动脚本,可以往下走、往上走,可以去各个房间,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。
但你会发现,这个环境还是有很多缺陷,能学到的局限在这个环境,这个环境还是不够大。而且你如果用RL学这个环境,就会像用RL学传统的视频游戏,可以把这个游戏打通关,但对于其他任务没有迁移作用。你可以把围棋下得特别好,但对世界上其他事情没有价值。
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环境。
张小珺:你博士期间的研究工作:语言智能体(Language Agent)、ReAct(浏览维基百科进行推理)、Reflextion(反思)、Tree of Thoughts(思维树)、digital automation(数字自动化)、WebShop(网上购物)——这些研究跨度很大,它们的共性问题是什么?你是怎么按着兴趣一步一步延伸的?
姚顺雨:从我的角度,是非常自然的过程。当我意识到环境有问题,我第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是WebShop,首先要解决环境问题。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任务或环境,把这个游戏刷得再高,没有意义。
2015年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叫World of Bits(比特世界)。当时想法是,我们应该把电脑或互联网作为一个环境,这个环境比游戏更exciting(令人兴奋)。但因为各种技术限制,没有做得特别好。到2021年,我和导师讨论,觉得这时可能是一个自然的时间点重新去做。
我当时也觉得,技术还没完全成熟,大多数人还在研究一些比较标准的任务:a能不能导致b,或者翻译,或者从一篇文章回答问题。那个阶段想做互联网上的Agent,技术还没ready(准备好)。但也正因为技术没成熟,反而是一个好的时间点开始做。到2022年,我们就做了WebShop这个环境。
2022年,GPT-3.5发布,还有后来Chain of Thought(思维链)出现,带来新的方法层面上的机会。我们就做了ReAct这个工作。我现在还是觉得,我自己最喜欢的工作是ReAct。
之后,基于这两个方向:一方面做更多方法(method),一方面做更多任务(task)。
但总体来说,我的研究有两个核心:
张小珺:ReAct的提出标志了范式的变化吗?
姚顺雨:这需要5年或10年以后再去看。
当时学术界还不太能接受,我去做一个prompting(提示工程),把它作为research(研究)。传统意义上,你需要提出一些fancy(花哨)的东西——需要提出一些数学公式,训练一个模型,证明很多理论,或者做很多工程上的事。但如果你只是去用一个模型,感觉太软了。
不过,当时最有价值的,就是去研究怎么使用模型。如果你想训练模型,会落后OpenAI或这些公司好几年。你做的很有可能几年前别人已经发现了。如果你想做不一样的,可能怎么去使用模型更有价值。
张小珺:为什么你做这件事情比大部分人都早?
姚顺雨:有幸运的部分,我PhD做的第一个事就是基于语言模型做Agent。当时做的人很少,因为它太难了,或者不是一个共识类的事情。当时共识类任务是做问答,做翻译,或者做一些已经被社区接受的任务。
我一直有这个非共识:我想要去做Agent。
另一点是,我一直想做简单且通用的东西。我不想做一个很复杂、但只能在一个领域奏效的东西。这个方向在传统意义上很难被接受,大家习惯了做AI的方式:把问题不停细分,做很多细分方法。
可能并没有多少人想做一个简单且通用的系统,或者认为这是可能的——尤其20年之内。
第二章 系统
02 机器的手
“人最重要的affordance是手,AI呢?”
张小珺:今天我们的话题是Agent和强化学习,我们很好奇你会怎么定义Agent?
姚顺雨: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要结合讨论背景看。
从自然语言处理的角度,Agent是相对于一个只会生成文章或对话的系统而言。它能和外界交互,比如使用计算器、互联网,或调用各种工具。也就是说,不仅能生成内容,还能操作和互动。
但从更广义的AI背景看,Agent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概念。
任何能进行自我决策、与环境交互,并试图optimize reward(优化奖励)的系统,都可以被称为Agent。
从这个角度出发,今天我们讲的Agent更多是指:怎么基于语言模型这样的foundation model(基础模型)去做具备自我决策能力的系统,而不是传统意义上基于规则或仅在某个领域用强化学习(RL,Reinforcement Learning)训练出来的Agent。
因为“Agent”这个词在不同时代有不同定义——你可以说AlphaGo是Agent,也可以说Waymo是Agent,甚至可以说机器人是Agent。这个词的意义很依赖具体情境。
张小珺:你研究的“Language Agent”(语言智能体)和传统Agent,存在本质区别吗?
姚顺雨:本质区别是可以推理,因为推理才可以泛化。
举个简单的例子,我做ReAct一个很强的动机是:我做完colm,我的第一个工作之后,在思考一个问题——为什么我可以一下子去玩一个新的游戏,但现在这些系统或AI需要几十万步甚至几百万步训练,才能完成类似的事?
我发现,是因为我可以思考。我看到一个全新的环境,会想:这个灯是黑的,那可能有危险,基于常识可能有怪兽;我现在最重要的是点亮灯。基于之前的上下文(Context),灯在我后面,那我应该先向后走。
如果没有这样的思考能力,而是直接从复杂语言去预测“我要往后走”,就很难——没有推理做不到。
最大区别在于,语言模型提供了一个足够强的先验(prior),这个先验让你可以推理,而推理又可以在不同的环境间泛化。
所以核心是推理能力,推理才能带来泛化。
张小珺:从你的视角看,Agent是一个怎样的演变历程?它是怎么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?
姚顺雨:我可以说一下自己的理解,可能不完整,或者有一些错误。
最早的AI,我们称为Good Old-Fashioned AI(符号主义AI),想法很简单:我注重的是推理,我怎么想,就把这些规则写出来,让AI也这么做。比如,如果温度高于30度,空调就应该降温。这种基于规则的AI,可以造出很多早期智能体,比如最早的机器人、最早证明数学定理的系统,很多是这么做出来的。
但很快,1980年代,大家发现这个东西有瓶颈——你不管写多少规则,还是很难覆盖这个世界上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。
那时符号主义走向极致,大家开始做专家系统:找很多专家,把这世界上所有可能的规则都写下来,是不是就能得到AGI?或者一个通用的、有用的系统?
但后来发现,无论你写多少规则,还是有很多特殊情况无法处理。这些规则只能用于一个任务。比如你写了一个诊断心脏病的系统,写了很多规则,但人千变万化,你没办法处理所有情况,这个系统也没法处理肺病。导致了第一次AI寒冬。
后来我们有了新的神经网络(Neural Network),也就是第二波Agent兴起,标志是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(深度强化学习)。典型事件是DeepMind玩视频游戏、做AlphaGo,OpenAI玩机器手、打Dota。
这一波核心是:我有一个虚拟环境,可以无限次尝试,有奖励机制,还有通用网络架构,我就像黑盒一样去学怎么maximize reward(最大化奖励),它就变强了。
这个方向取得了很多成功,最有名的是AlphaGo。但还是有老问题:每做一个新环境,都要做很多Environment-Specific(环境特定)工程。比如做Dota,要调很多参数(parameter tuning),做很多基于这个环境的工程。最大问题是:这些方法没法泛化。
你学了一个围棋Agent,没办法玩别的游戏。你在一个环境里学到的东西,没办法迁移到另一个环境。这肯定是不理想的。而且,如果你所有能解决的问题都在虚拟环境里,或者是像游戏那样可以无限次玩的环境,你就没法找到很好的真实世界应用。
第三波Agent是从大语言模型开始的。我们发现它可以做推理,而基于推理,就能进入一些新的环境,比如编程、互联网、各种数字环境。这些数字环境有一个共性:大多数都是基于语言的,需要推理。
这一次Agent的核心区别有两点:一方面是方法上,我们使用语言模型,用推理去构建能处理各种问题的Agent;另一方面是环境本身也发生了进化,从早期符号主义环境(比如数学定理),到下围棋、打游戏,再到今天互联网、编程、电脑操作这些更接近真实世界的数字环境。
所以这是两条线:一条是方法线,一条是任务线。
大家可能更多注意到方法线,容易忽视任务线。但这两条线是相辅相成的。
张小珺:我一直有一个基础疑问。OpenAI提出的大模型能力分级从Level 1到Level 5,很多人都很熟悉了:
但这个五级划分的内在逻辑是什么?为什么是先有聊天机器人、推理者,然后才是Agent?Level 4和Level 5又是怎么来的?它们之间是递进关系吗,还是各自独立发展?
姚顺雨:逻辑是,首先你要有语言的先验知识。基于语言的先验知识,最早能做出来的应用是Chatbot(L1)。接下来,基于语言先验,你需要具备推理能力,这是Reasoner(L2)。
当你既有语言知识,又具备推理能力,才可能进一步做各种Agent(L3),尤其是能泛化的Agent。也就是说,Agent建立在Chatbot和Reasoner能力之上。
很明显,今天Agent发展最关键的两个方向:
这两个方向,我觉得是正交,它们可以并行发展。
谁是Level 4,谁是Level 5,我不确定。但这两个事情是显然的下一步。
张小珺:从Level 2到Level 3,也就是你做的这一步——从训练模型到使用模型,是一个很重要的跨越。
姚顺雨:或者说,是从单纯做推理,到把推理应用在Agent上,用它去和环境交互。
张小珺:Agent目前有哪些主流架构?形成共识了吗?
姚顺雨:我的感觉是,大多数时候大家用的还是类似ReAct架构。你能够去推理,然后你可以产生action(行动)。这是最简单的一种形式。但最简单的反而是效果最好的。
当然,基于不同任务,大家会设计很多workflow(工作流)或更specific(特定)的方法。但如果说最通用、适配性最强的方案,我还是觉得是类似ReAct的方法。
李广密:提升Agent能力,你自己最看重的是哪几个关键能力?
之前有人提到Context(上下文)、Long-Context Reasoning(长上下文推理)、Tool Use(工具调用)或Instruction Following(指令遵循)。你刚才一直强调Reasoning(推理),那如果要提升Agent的能力,你最在意哪些能力维度?
姚顺雨:这是个很好的问题。我觉得现在没有一个特别成熟的taxonomy(能力分类体系),或划分系统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方式。
有些人会按照工具划分,比如coding(编程)能力、上网能力、使用计算机的能力,这是一种划分方法;另一种是按照模型自身的能力划分,比如多模态处理、长上下文处理、推理能力——这两种划分都有道理。
但就我现在看,我最看重的是Context(上下文)处理能力,或Memory(记忆)能力。因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,才能进一步实现Lifelong Learning(终身学习)或Online Learning(在线学习)的能力。
李广密:你刚才一直在提环境,你认为code代码是一个实现AGI最重要的环境吗?它可以支持多轮的强化学习(RL)、提供闭环反馈,也可以验证结果。如果我们在代码这个环境上构建Agent,会不会发展更快?
姚顺雨:毫无疑问,这是最重要的环境之一。
Code有点像人的手。
它某种程度上,是AI最重要的affordance(环境给予行动者的可能性)。
对于物理世界,人最重要的affordance是手——我们围绕它制造各种工具,比如锤子、笔、筷子。但对AI、对Digital Agent(数字智能体)来说,最重要的affordance可能就是code。
因为其他东西,都是给人定义的。比如网页、小说、视频,是为人类设计的;但code是一个天然就给机器使用的表达形式。
我2022年一直在想:做Coding Agent明明是很重要的事,为什么没人做?
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工作叫InterCode。大家都在做的是:给一个coding task(编程任务)模型生成一段代码,然后你去evaluate(评估)它。但我们就在想:为什么不把执行结果反馈给模型?
我们可以让它变成一个多轮Agent task(智能体任务),构造成一个环境,而不是单次完成的任务。基于这个,我们后来做了SWE-bench、SWE-Agent。
有时候,很有意思的一点:一个东西明明非常重要,但就是没人做。如果你是一个研究员,觉得你做的事很重要,但别人不觉得、也没人做,并不是坏事——可能它真的很重要,只是大家还没开始。
李广密:这里有个很强的非共识:有的人觉得code是这一轮技术革命最大的价值体现,但也有人觉得可以泛化到更多任务里,在电脑、手机、数字世界中都可以实现,Agent操作人能做的95%、99%任务。
你对从code到数字世界这一步的跨越,或者它的泛化,是有信心的吗?
姚顺雨:更广义说,你可以认为API也是code的一部分。任何基于code的接口,都属于code环境的一部分。
有个非常经典的debate(争论):最终的AGI,是基于API或code的?还是基于GUI(图形界面)?或者是为人定义的前端环境?还是它是一个混合体(mix)?
这个问题有点像:你是想改造你的车让它适应所有路,还是改造所有路让它适应现在的车?
很多时候,现实中并没有现成的API,只有GUI。但你可以人为为它构造一个API。
当然,最终结果很可能是meet in the middle(在中间相遇),两边都会做,而且这个事情可能没那么难。
现在看,让一个Agent既能使用code,又能操作人类界面的screenshot(截屏)、前端,两者兼顾也没那么困难。从这个角度说,让Agent像车一样能适配各种路,比起要改造所有路让它们都有API,要容易很多。
Coding肯定很重要,但如果让Agent也能操作GUI,最终Agent很可能是“什么都能做”的。
03 任务的设定
“我们对简单任务的robustness没有重视”
张小珺:你4月发布博文《The Second Half》(下半场),你是怎么想到the second half这个idea的?受了什么启发吗?
姚顺雨:我是受邀去斯坦福一门课做talk,当时想,能讲点什么?没法讲太技术,只能讲更哲学的内容,就想到这个话题。
这个想法来自我在OpenAI的工作经验,以及之前做research的感悟。大家过去往往更关注模型训练、方法设计,但我觉得现在的bottleneck(瓶颈)已经转移了:变成怎么去定义好的任务,怎么去定义好的环境。
张小珺:现在是处在那个转折点吗?从上半场到下半场。
姚顺雨:主线正从“上半场”转向“下半场”。我说的主线是基于语言的智能体。当然你也可以说,在Audio(音频)、Multimodal(多模态)、Robot(机器人)这些方向,还有很多未解的问题。
但我觉得,从语言出发,去定义Reasoning(推理)、定义Agent,我们终于有了一个非常general(通用)的方法,而且这个方法是可泛化的——我们实现了一个基点时刻。
这带来一个本质变化:以前我面对很多怪兽,需要造出各种不同武器去打它们;现在我有了一把通用武器,比如机关枪,我不需要再为每个怪兽单独造武器。接下来要思考的问题就变成:我该朝哪个方向开枪?
现在方法的问题已基本解决,真正重要的是——我们要用这个通用方法,解决什么问题?
李广密:怎么设定任务?怎么定义问题?关于这个,你在探索过程中有什么思考吗?
姚顺雨:不同的人有不同的flavor(风格),我从很早就有一个偏好:我想定义一个基于结果的reward(奖励),而不是基于过程的;而且这个reward应该是基于规则、可计算的,而不是来自人的偏好、模型的偏好,或者一些黑盒指标。
我们做WebShop的时候,最困难的一点是,怎么定义reward。我觉得做任何RL(强化学习)任务最难的不是建环境,而是怎么设计reward。你当然可以把Amazon或Facebook模拟出来,工程上确实很难,但总是可以做。但最难的,是怎么设计一个既有难度,又有实际价值,同时又有一个好的reward的任务。
我希望这个reward是不noisy(不噪声大)的,是可解释的,是白盒的(white-box),不是那种黑盒的东西(black-box)。
事实证明,这也是现在RL成功的关键。像math(数学)和coding(编程)这种任务,之所以能做出来,核心就是:
比如,一个数学题答案是3,它就是3——只要你得出的是3,就是对的;不是3,就是错的。
但如果你reward是基于过程,就会出现hacking(投机取巧)。你去优化人的偏好、模型的偏好,也会出现hacking。比如你生成一段非常优美的代码,但它并不解决实际问题。
我后面做的很多task,也都是用同样的filter(筛选标准)。
比如SWE-bench这类工作:
张小珺:就像上面说的,OpenAI有5个分级。如果从任务定义出发,是不是也可以做出一套产品能力的分级?随着模型能力溢出,我们开始使用这些能力,Agent能力可以怎么分级,你脑海中有没有一个初步的框架?
姚顺雨:我现在倾向于认为,不同类型应用会带来不同challenge(挑战)。这些挑战是正交的,很难说哪个更难、哪个更简单。
人类也有这个问题——洛克菲勒和爱因斯坦谁更厉害?很难定义;成为一家大公司CEO和成为一个数学家,哪个更难?只是不同的挑战类型。
而对于Agent,另一点是:人觉得很简单或难的事情,对Agent可能不是那样。
人觉得做客服比做软件工程师简单很多,工资也低、文凭要求也低。但现在反而做软件工程对Agent更容易。因为软件工程有更好的环境、更清晰的reward、更大的数据量,等等。但你想做一个特别robust(健壮)或reliable(可靠)的客服,反而更难。它涉及复杂的reliability challenge(可靠性挑战)。
我们当然可以把人类工作分成不同的category(类别)。但对AI来说,人类觉得难或不难的任务划分,不一定直接映射到AI的能力上。
张小珺:整体来说,什么样的任务适合Agent做?什么样的任务适合人和Agent一起做?什么样的任务适合人做?
姚顺雨:我现在感觉任务大概可以分成几类。
一类任务更注重reliability(可靠性)。你做客服,重要的是:100次里你需要99次甚至更多不能出错。你只有85次让用户满意,还有15次不满意,可能被炒鱿鱼。这种任务比较简单,但需要极高稳定性。Agent就需要特别强调reliability。
另一类任务更注重creativity(创造力)。你去证明黎曼猜想,或者写一个复杂程序,或者创作一部文学剧本。这类任务允许你失败很多次,只要有一次做得特别好,就算成功了。这是非常不一样的挑战。
还有一种划分方式是:看任务的深度和广度。
有些任务像Cursor(一个代码编辑工具),是非常短的loop(循环)。我只需要把一个文件改一下,可能3秒就完成。但也有一些任务需要30分钟、3小时,甚至3天。这种任务需要的是Long-Term Memory(长期记忆)的能力。
再比如,从任务的广度看,我只是去解决一个具体bug,这是比较窄的问题。但如果我要从0搭建一个像Windows这样的操作系统,这是一个非常广的任务。你可以说这是一个人能做的事情,一个小组能做的事情,还是一个公司才能做的事情?从这个角度,我们也需要做更多motivation research(动机建模研究)。
张小珺:哪些任务对于Agent是相对更好定义的?从易到难的顺序应该是什么?
姚顺雨:我们可以平行做很多不同事情。有一个简单的设计评估指标(metric)方法。
在coding任务中,我们传统有一个评估指标叫Pass@k,意思是:你对同一个代码生成任务,最多尝试k次,其中起码有一次的成功概率是多少?你可以想象,当这个k越来越大,系统被使用的成功概率也会变大。
很多时候做coding相关研究,它会report(报告)的是Pass@100,也就是:同一个任务你跑100次,起码成功一次的概率是多少?
但我们2024年发了一个研究,叫TAU-Bench(Tool-Agent-User Benchmark,工具–智能体–用户基准测试),想法是:对于另一类任务,比如客服,我们需要一个刚好相反的指标,我们把这个指标定义为Pass^k。也就是:每一次都成功的概率是多少,或者失败一次的概率是多少?
有些任务我们需要优化的是Pass@k(多次尝试中至少成功一次),而另一些任务,比如客服,我们需要优化的是Pass^k(每次都成功),或者我们最关心的是Pass@1(一次就要成功)。
但是,现在我们对于简单任务的robustness(稳健性)并没有特别重视——这是因为大家做AI还是在做一些benchmark(基准任务),而不是实际应用。
但如果你接受了这个mindset(思维)转变,很自然你就会意识到:有些应用是需要特别强调robustness的,那你就需要去优化它的robustness。
现在大家还没完全意识到这件事;但我相信,如果大家意识到这个转变,会带来很大进步。
04 泛化的工具
“语言是人为了泛化而发明出来的工具”
张小珺:你有一句非常high level(抽象)的总结:语言通过智能体中的推理实现了泛化。这里的泛化是一个已经被证实的,还是一种推断?
姚顺雨:为什么语言非常独特?因为它是人在这个世界完成各种各样事情的工具。
语言也是人类发明的工具,像火或笔一样。但它之所以特殊,是因为它是一个帮助你解决任何事情的通用性(general-purpose)或泛化性(generalizable)的工具。
当你学会了这门工具,你可以去做很多新任务。比如你学会了攀岩,它帮不了你完成新任务。但你学会了语言,你可以通过语言和人交流,学习、思考、推理。
2020年以前,大家没把这个事想清楚,觉得语音、文字、图像、视频都是一些数据,没什么区别。但我觉得最大区别是:语言是人为了实现泛化而发明出来的工具,这一点比其他东西更本质。
张小珺:这里说的是语言具有泛化能力,那么强化学习终于具备了泛化能力,这是一种推断还是一种结论?
姚顺雨:可以说是我个人观点,当然很多人在讨论。泛化与否,本质上是一个spectrum(谱系)问题,是一个相对概念,不是绝对的0和1。
我之所以这么说,是因为在此前,如果你在一个特定环境上训练,模型只能在这个环境表现良好,不能轻易迁移到其他环境。但现在,你在一个环境上训练,模型可以适应更多不同环境,这才是最本质的区别。
DeepSeek大家觉得一个有趣结果是:你在数学和编程领域用强化学习训练模型,但它在创意写作上也变得更强。
这体现了本质区别:AlphaGo只能下围棋,不能下象棋;而现在你学会数学,也能提高创意写作。
李广密:我读你的文章,印象最深的也是,你提到RL终于泛化了,是真的泛化吗?——你刚才也说,有很多先验知识已经train(训练)到model(模型)里头了,有什么迹象让你感觉是真的泛化了,而不是training data(训练数据)里面就包含这些数据?
姚顺雨:对,我觉得是有可能的。如果你的Pre-Training(预训练)已经包含了所有事情,那么 RL(强化学习)只是激发出这些能力的skill(技能)。
事后想起可能是Ilya(OpenAI前首席科学家),还是谁,说过一句话,意思是:Maybe the ultimate generalization(也许最终的泛化),就是你去overfit(过拟合)现实。如果你能把剩下的所有事情都做完,那么讨论它是过拟合还是泛化就不重要了。
但我觉得,它还是泛化的。原因是它能够推理。当你能在一个环境学到如何思考的技能,并且这种思考能力能迁移到新环境,这才是泛化的本质原因。
李广密:训练某一类游戏变强,能泛化到其他游戏也都很强吗?比如,一个模型打Dota(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)非常强,是不是在所有游戏里都很强?
姚顺雨:不好说。即使是推理,它在不同环境的泛化能力也可能不一样。比如,基于逻辑的推理,可能从数学到编程的迁移更容易;基于人情世故的推理,可能在另一类任务上迁移得更好。
但重要的是,现在终于有可能出现一个单一模型能够做所有任务。之前认为这不太可能,但现在是有可能的——你可以在很多不同任务上做强化学习,而且它能迁移到更多任务。
当然,如果只考虑任务与任务之间的迁移,迁移程度和任务本身的性质有关系。
李广密:代码和数学之所以容易泛化,你有想过背后的原因吗?是因为他们有思考过程?
姚顺雨:只是因为它是最早开始做的。它之所以最早开始做,是因为它相对简单,有一个很好的reward(奖励信号),不需要复杂环境,它本身就是推理。
现在看,很多其他任务也是可泛化的。只是我们一开始做的是这个任务,所以,大家对这个方向的讨论比较多。
05 奖励的机制
“当AI玩一个语言游戏,
要怎么定义内在激励?”
张小珺:基于基础模型往上长,Agent生态树在你脑海中,会是一个怎样的结构?
姚顺雨:一个方向是:fundamental research(基础研究)怎么演变?或者说,方法怎么演变?
另一个方向是:应用,或者它的交互方式(interaction)有怎样的演变?
这两个方向之间有关联。但它们需要不同的人去探索不同的方向。比如Cursor并没有在fundamental research上做什么创新,但做了交互方式上的创新。
在fundamental research上,比较重要的有三方面:
这也跟OpenAI提出的Innovator(L4、创新者)和Organization(L5、组织者)框架很像。
你作为一个Innovator,首先你需要一个Long-Term Memory(长期记忆)。
比如,我是Wiles(安德鲁·怀尔斯,数学家),我研究费马大定理,可能花了20年。我就需要一个长期记忆。
我有这个长期记忆还不够,还需要有内在的reward。因为在你真正证明那件事之前,没有任何外部奖励(Extrinsic Reward)——你没有获奖,没有做成任何“可交付”的事情,也没人给你feedback(反馈)。你需要自己给自己反馈。
这是所有Innovator最重要的。无论你是艺术家、科学家、文学家,还是任何类型的创作者,对吧?
另一方面,作为一个Organization(组织),你需要解决的问题是:Agent和Agent之间怎么协作?怎么让Multi-Agent(多智能体)协作scale(规模化)?
现在的Agent就像一个普通大学生,做一个数字化的实习生。或者说,AGI就是一个普通一本大学生在电脑上能做所有事情的一个能力。
但是,人类社会的边界是什么?这当然覆盖80%或90%的人。但我们最崇拜的人,是哪两种?
很自然,个体的创造力和组织的协作能力——都非常重要。
张小珺:为什么OpenAI分级的最后一级是组织者(L5)?
姚顺雨:我一开始是认为Innovator(L4)和Organization(L5)是更正交或并列的关系。
我当时在群里问了一个问题:当一个大公司CEO和一个科学家,到底哪一个难?
这个不好说,实现路径有区别。所以,不用太纠结谁是第四级,谁是第五级,都很重要。不一定要先实现哪一个才能实现另一个,可以同时去探索。
李广密:这中间有几个关键的问题要突破,比如长期记忆,这是短期可预期突破的吗?
姚顺雨:也许吧。当然也取决于多短期?但我觉得当它足够有价值,它必然会突破——如果你对技术是乐观的。
李广密:长期记忆,你要展开讲一讲吗?
姚顺雨:我不知道我能分享多少,但我的信念是——是Utility(效用)的问题。
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模型,推理很强,考试很强,玩游戏很强;但它还没创造出足够经济价值?——根本原因是:它没有这些Context(上下文)。
人类社会比较 tricky(复杂微妙)的一点是:当然,我们确实写下了很多东西——我们用文字、Google Doc、Notion,记录了很多东西;但很多Context永远只存在人的大脑,是通过一个分布式的系统来维护。
比如,你老板跟你之间的行为习惯,或者一些很难用语言总结下来的信息。这些Context存在于人的脑海里。人没办法把这些东西全部写下来。
这就导致——人是不可或缺的。
只有人有这样的能力:进入一个环境,获得这个环境里的Context。
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,Utility问题就可以在很大程度被解决。这个世界,大多数人并不是乔布斯,也不是爱因斯坦,只是一个普通人。他的数学推理没有o3强,但他能manage Context(管理上下文)。
他去一个公司7天,除了在文件上看到信息外,脑子里也积累了Context。而这些Context是o3没有的。虽然他没有o3聪明,但因为他拥有Context,他做得比o3好。
李广密:有可能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最强的软件工程师,甚至2027年看到能操作人类电脑、手机上几乎所有任务和指令的通用Agent,你对这一天的想象是怎样的?是过于乐观还是比较合理?
姚顺雨:现在还没有well-defined(明确定义)。现在模型写代码的能力超过世界上几乎所有人,或者说,它的数学和逻辑推理能力,也比大多数人强。但是,当你说它能不能很好使用环境,关键还是看你让它做什么任务,这个任务能不能被合理定义。
很多时候,人类最难的问题不是推理本身,而是获得完整Context(上下文)。
现在模型的bottleneck(瓶颈)不是缺少推理能力,或者写代码、使用前端的能力,而是缺少一个完整的上下文。
我不知道这是Intelligence(智能)问题,是产品问题,还是别的什么问题——但如果想让AI真正发挥价值,这个问题必须解决。
李广密:你刚才提到另一个关键点:模型或Agent要有内生奖励系统。今天是不是还没有这样一个系统?如果我们真的要赋予它内生奖励机制,是不是在它持续自主学习中,就可以改动自己的模型权重,从而更聪明?
我们离这一步还有多远?
姚顺雨:我不知道。我觉得会有这一天,但很难预测时间。
当然,它自我提升的方式,也许是改变自己的权重,也许是拥有一个基于语言的长期记忆,也许是一个基于Embedding(向量表示)的长期记忆,或者其他形式的记忆机制。但我相信,它会自我提升。
李广密:内生奖励,你能讲讲吗?
姚顺雨:就像我刚刚说的,很多创新者之所以能在没有外在激励的情况下坚持,是因为他有内在的价值观或激励机制。
这个问题,AI和神经科学已经研究多年。婴儿是最典型的例子。他们拥有基于好奇心或自我激励的机制。很多婴儿会反复玩一个玩具,用嘴去咬一个东西,或者做一些看似“无意义”的动作。
你说他获得了什么reward吗?他没有升职加薪,没有拿到钱,没有任何外在激励——他只是好奇。他的动机是:“如果我做这个事,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?”如果这个感觉是新的、不同的,他就可以从中学习。
张小珺:他可以获得安全感。
姚顺雨:对,就是说,好奇心、掌控感、安全感,是一些内在动机。正是这些东西驱动了人去做某些事。否则,很难从纯粹理性角度解释:他为什么要做?
但有意思的是,当人长大之后,会发生重要变化。当你是婴儿,你对世界的理解,是基于视觉、触觉,基于物理世界的。你学习的是,怎么把触觉、听觉、视觉,以及对骨骼系统的控制结合起来。
当你长大之后,你对世界的理解方式变了,变成一个基于语言、推理、文字系统的理解。你开始思考: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?我怎么才能开一个公司?怎么才能升职?怎么才能做成一些事情?
你玩的,不再是一个物理游戏,而是一个文字游戏。
在这个文字游戏里,当然也存在内在激励,但又好像和婴儿时期的好奇驱动不太一样。
这是AI面临的挑战:传统AI,比如玩迷宫、做机器人仿真,它可以定义一些基于世界模型或者模仿婴儿阶段好奇心的内在激励。
但当AI在玩的是一个语言游戏,要怎么定义内在激励?——这个问题就变得不太一样了。
张小珺:你在文章也说,我们忽视了任务评估标准的重要性。应该怎么去评估?——比如,我们怎么去衡量一个Agent?有哪些北极星指标?
姚顺雨:还是要思考怎么去创造更多现实世界的价值。
当然这个事情在不同领域、不同应用下,有非常不同的任务设计、方法和路径。但有一个大趋势是:应该更多去思考实际价值,而不是这些被设计出来、类似考试或游戏的东西。
我们发现,一旦你可以定义一个考试或游戏,离它被解决也不远了。
甚至你可以说,世界之所以难,是因为它不是一个被设计出来的东西。考试和游戏有一个很大特征是:它在被设计的时候,就已经有一个很好的reward或标准答案。
但当你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reward或标准答案,再加上现在已经有一个general recipe(通用解法),那这个事情离被解决也不远了。
而真实世界的问题是:它没有标准答案,没有标准的reward function(奖励函数)。很多时候人做事情,也不一定是为了一个理性的reward,但人还是去做了。
张小珺:它是开放的。
姚顺雨:对,现在主要问题是这个。最大问题不在于,我有没有一个well-defined(明确定义)的答案,而是我怎么找到它。
张小珺:我们未来还需要更多地推翻各种各样的基本设定吗?
姚顺雨:我觉得需要。
人类一直在做这件事,不是吗?
第三章 吞噬的边界
06 双刃剑
“创业公司最大机会是:
设计不同的interface”
张小珺:你知道,应用型创业公司很担心,大模型公司的模型能力溢出,会把他们做的Agent吞掉。
长期看,Cursor这样的公司,壁垒是什么?哪些Agent是模型公司必然会做的?哪些有创业公司机会?——边界可能在哪?
姚顺雨:创业公司应该担心的是模型没有溢出能力,这样你就真的什么都做不了了。有溢出能力是个非常好的事情,这几乎意味着你有机会。
创业公司最大机会是:能设计不同的interface(交互方式),或者说人和数字世界交互的方式。
ChatGPT或所有做模型的公司,都在做类似ChatGPT的产品。ChatGPT的本质是:你是在像和人交互一样去进行和数字世界的交互。
你的Chatbot是像人一样的东西——你和他聊天,给他布置任务,让他帮你做Deep Research(深入研究)或者写代码——交互方式是像人,或者像助手一样的交互方式。
如果你能用模型通用能力,创造不同的交互方式,就能创造巨大的机会。
最终,可能模型的能力会产生beyond ChatGPT(超越 ChatGPT)的交互方式,变成Super App(超级应用)。
如果你做旧的interface,你利用这些新的模型,很容易被ChatGPT取代。如果你的交互方式很像ChatGPT,你有什么理由不被ChatGPT取代?如果你做的是新的交互方式,但模型没有继续变好、没有新的溢出能力,也很难做。
对于创业公司,最好的机会是:你做新的交互方式,并且模型不停有新的溢出能力,让你能够赋能这些新的交互方式——两者缺一不可。
张小珺:但是ChatGPT也可以跟进这个新的交互方式。
姚顺雨:对。但拥有一个Super App对于公司是双刃剑。
当你已经有了一个交互方式,你必然形成路径依赖。就像2020年Google有无限多资源和钱,有Transformer,但它最自然的想法是:我怎么用这东西提升搜索引擎?
当你有像ChatGPT这样的Super App,很自然你的研究就会center around(围绕)这个Super App,会center around这个交互方式。
你会探索新的产品,但即使是大厂,即使是谷歌,即使是OpenAI,大部分资源还是会围绕你Super App的交互方式——所以,这是创业公司的机会。
李广密:你刚才提到交互方式,今天还是人跟code交互、人跟text交互,那人跟Agent未来是怎么交互?你感觉Her会是一种正确的交互方式吗?如果这种交互奏效,有没有机会beat(胜过)ChatGPT今天的形态?
姚顺雨:Her是不是还是类似一个Assistant(助手)的形态?只不过它有语音而不是文字?
这是一个显然很有价值的形态,人和人交互已经几千年、几万年、几百万年,这是对人最自然的形态,肯定是最显然的Super App。
但这个生态位,我觉得ChatGPT是站住的。模型公司一开始做的就是这个。
那我觉得不显然的是:我能不能基于不像人的交互方式?
Cursor是很好的例子,创造了一种新的交互。不是像人一样的交互,而是像Copilot(副驾驶)。写代码的时候,它能给你提示或编辑。没有人和人是这样交互的。这是它的价值所在。
Google也是很好的例子。雅虎是一个更像黄页、更让人熟悉的交互。但谷歌是一个让人不熟悉的交互,很奇怪。
Assistant、Her,或者像人一样的交互方式,显然是最重要的交互方式之一,但还是会有足够多的机会,诞生新的交互方式。
张小珺:你脑海里有没有一些新的交互?非ChatGPT在探索的形态,也非传统互联网的交互,在你脑海里有吗?
姚顺雨:Canvas是一个好的尝试,可以基于现在的任务,在线生成最符合情境、个性和任务的前端。这是值得探索的方向,但也很难。
李广密:在你看来,应用公司的数据飞轮,对他们来说重要吗?或者说,在什么环境下才能形成?
我感觉,Chatbot产生的是偏好数据,好像没什么数据飞轮;Code可能有思考过程的数据,这种思考过程的数据代表一类能力,可能是有用的;像Canvas也好,Artifacts也好,可能是有思考过程的数据,这类可能有机会形成很强的数据飞轮效应。
姚顺雨:大多数公司还没有形成数据飞轮;他们依赖模型变好,利用模型变好的溢出能力。
如果你要有数据飞轮,首先你要能自己去训模型,并且能通过交互有很好的reward,使你能把好的数据和不好的数据分开。
比较成功的是Midjourney,有非常清晰的reward——人更喜欢哪张图,这个reward和应用是对齐的,reward做得更好,公司就更成功,模型也更好——一切都对齐。有了这种情况,才能自己训练模型,做数据飞轮。
这个过程必须比较非主线。因为如果很主线,我也可以通过Pre-Training或RL提升能力,靠泛化或其他方式。
总的来说,大部分公司目前还没有形成飞轮。
07 对Agent创业者的思索
“这世界是相互抄的关系,
而不是单向抄的关系”
李广密:在你看来,Agent创业者一定要有研究背景吗?
姚顺雨:不好说,挺看人的。很难把人简单分成research和非research两类,没那么泾渭分明——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很大。
可能最重要的一点,还是得找到value(价值)。不管你叫它product-market fit(产品与市场契合)、产品的sense,还是别的——找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最重要。技术只是手段,目前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,需要找到一个好的问题。
如果你有很强research背景,比如自然语言处理,反而可能是坏事——因为你会对技术太执着,拿着锤子到处找钉子。
Cursor创始人是四个本科生。Perplexity创始人是研究员出身。真的挺看人的,跟你是否做过research,没有那么强相关性。
张小珺:好的AI产品经理应该长什么样?
姚顺雨:好的AI产品经理就是一个好的产品经理,可以第一性思考。AI是变化很快的,相对不变的是人、人性、人的需求。这变化得更慢。
你能找到一个好的需求,从第一性原理反推:要把它做成,我需要应用什么样的技术?
张小珺:你怎么看Manus、GensPark这些产品和他们的创始人?
姚顺雨:我试过Manus,还没试过GensPark 。Manus挺有意思,给我一些启发。他们产品sense很好,有打磨产品的基因。
张小珺:这个产品应该是OpenAI主线上的产品对吧?
姚顺雨:Emm……You will see。
基于Manus,我再讲一点。传统大家认为发生的事情是:我大厂先做出来一个东西,创业公司就可以开始抄。比如做出ChatGPT,我可以去抄一下ChatGPT,做一个类似的事情。
但现在,似乎反过来也可以成立。可以先小厂做一个事情,它创造出来一个交互的创新或者产品的创新,做模型的公司也可以去借鉴或者应用。
这点还是挺有意思。很多时候大家会说,模型做得越来越好了,是给创业公司做嫁衣了。因为你创造很好的模型,如果没有自己运用特别好,这些创业公司就用好了。
但也可以反过来,如果你创造一个非常好的交互,但没有能力把模型或底层能力做特别好,大公司也可以借鉴你的交互,再加上它的模型能力,做得也特别好。
这世界是个相互抄的关系,而不是一个单向抄的关系。
李广密:如果你是Manus创始人、CEO,你今天要走向垂直方向吗?
姚顺雨:Manus的一个价值是,它给人非常general(通用)的感觉。但我觉得,有一个非常通用感觉交互方式的Agent,和你有一些Killer App(爆款应用),是不矛盾的。
一个比较理想的情况,你有一个非常通用的交互方式,这个交互方式想象力足够大。比如Cursor,虽然它是IDE(集成开发环境),如果它只做 IDE,想象空间是有上限的,就在IDE里面。但如果你做一个非常general的产品形态,比如Manus,想象空间是很高的。
但并不矛盾的是,你可以有每个阶段的Killer App。比如它做PPT特别好,做Deep Research特别好,或者做其他东西特别好。
iPhone或iPad是非常通用的产品形态,但它一开始,都有一些Killer App支持它有momentum(增长动能)。包括ChatGPT,包括微信,很多伟大产品都这样。
你有一个足够通用、简单,或第一性的交互方式,它有很多想象空间。但你去维护它,或者设计路径的时候,你能有各种各样的应用,使它不停地增长。
张小珺:你听了我和肖宏(Manus创始人)的播客,有什么感觉吗?
姚顺雨:我觉得挺有意思。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说,VC是一个非常贵的融资方式,不是在你不好的时候,而是在你好的时候。他有很多挺不一样的思考问题角度。
张小珺:2025年过年DeepSeek全球爆火,这对硅谷的AI研究员带来了哪些叙事变化?
姚顺雨:从OpenAI角度,大家讨论的有几点:
一点是Chain of Thought(思维链)的reveal(展示)。显示出一条长的思维链,似乎很重要,它是产品形态的突破。很多时候,技术积累已经到了,就像洪水已经到达闸口,需要一个时刻“开闸”,让大多数人真正感受这个技术。
我们会说有iPhone moment、ChatGPT Moment,可能有DeepSeek moment。这个moment就是指,一个非常大的交互方式上的冲击,带来了magical(神奇)的体验。
另一点是对开源的重新思考。Sam(OpenAI首席执行官)在他Twitter上讲了很多,说OpenAI过去忽视了这件事,但仔细想一想,它是有价值的,可能应该做。
我们默认认为开源落后于闭源,原因是,它不像 Linux(操作系统),我有1000个人可以每人出一份力,让系统通过分布式变得越来越好。做好一个强模型更像我有20个特别厉害的人,再加上大量资源,就可以做得很好。它需要非常特殊的组织、资源和人才集中。
这种情况下,传统意义上开源的优势没有那么大。比如Facebook在开源上,做得也没有那么好,在美国很多人也习惯性忽视这个路径。
做好开源是一个“很吃亏”的事。你首先要有足够的资源,有很强的人,有很好的组织文化,还要有商业上的justification(正当性)。最好情况是:你是个慈善家,有几百亿美金,你就做这件事造福世界。
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,但它发生了,就有这样一个人去做了这样一个事。
DeepSeek在许多方面,组织架构、工程能力、基础设施,确实有值得称道的地方。
张小珺:有一个Agent创业者想问你:Agent如何scale up?现在的主要瓶颈是算力,Agent的token用量非常可怕,单个用户消耗可能是Chatbot的500到1000倍,再叠加几百万个用户,成本非常高。这种情况下,Agent应该怎么扩展?
姚顺雨:最重要的点是——你得先找到一个好的应用。
Cost(成本)本身不是最大问题,问题是你的成本并不能证明你的performance(性能)或value(价值)是合理的。
如果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事,我花500美元,但可以赚1000美元——根本不是问题。这不是technical bottleneck(技术瓶颈),而是product-market fit(产品与市场契合度)的问题。
所以,现在最关键的,是要找到真正有价值的应用。模型的cost会下降,能力会提升,这个方向是确定的。但能不能找到那个有value的点,是最本质的问题。
当然,不同的应用,做法可能会很不一样:
总的来说,第一步永远是:找到一个真正有价值的场景。
一旦你找到它,cost的问题总是有办法解决。
张小珺:你在OpenAI的一个好处是不是,可以很清楚知道哪些是模型公司的主赛道,哪些领域可能是创业公司的机会?
姚顺雨:每个公司一旦有它的Super App(超级应用),所有事都会围绕Super App。当你有ChatGPT,训练模型的方式、组织架构,都会围绕ChatGPT重构。
如果你做一个和ChatGPT形态很不一样的东西,是会有机会的。
08 既单极又多元的世界
“这个世界不是单方压倒另一方,
双方都有自己的力量”
张小珺:一位AI研究者说,他对Agent的想象很有限,希望你能对未来的Agent畅想一下。你曾经说过,你的终极理想是打造“世界上最强的Agent”,它会是什么样的?
姚顺雨:大多数人对AGI的想象就是一个模型,就像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,他拥有所有知识、能力,比我们都聪明,是最强智能体。
但我现在的感觉是:不同的交互方式下,有不同“好”的定义,有不同“强”的边界。
最终的智能边界,是由不同的交互方式决定的,而不是由一个single model(单一模型)决定。
想象空间非常大。就像一开始互联网诞生,最早Super App只是把邮件升级成Email,Amazon已经算非常创新的东西了。现在就像那个阶段——我们的想象力仍被以往的交互方式所限制,还有许多尚未诞生的交互方式。
这些全新的交互方式,会改变我们的世界。
张小珺:在你脑海中,最强的Agent应该是什么样?
姚顺雨:对于不同的任务和交互,需要不同的Agent系统去解决。
模型是可以share(共享)的,但如果你讨论的是整个系统,那就不一样了。就像你问,这个世界上最强的互联网网站是什么?最强的互联网公司是什么?很难回答。它是一个multiface(多面向)的系统,有很多不同侧面。
AI可能也会变成这样的结构。OpenAI可能会成为一个类似Google的公司,成为新世界里非常重要的一环——但这并不代表,这个世界就会被这样一个单极系统垄断。
如果真是那样,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很灰暗。大多数人也就没什么价值了。
张小珺:你对未来Agent生态的构想会是什么样?现在有点像,当年大家都在创业做App的时候,如果再往后推演几年,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?
姚顺雨:很难说。但肯定会有很多不同的交互方式,创造出不同的系统。
OpenAI这样的公司,会想继续推进一个中心化的助手系统,有更多环境、更强能力,做更多事情。
也会有不同的生态系统,有不同的交互方式,会训练完全不同的模型。甚至从Pre-Training开始,所需要的能力和很多东西都不同。
比如,另一种交互方式可能是,我想造一个朋友。这个朋友不需要数学、物理特别强,数学太强反而不自然。它记忆不一定特别好,会犯错,有感情,也不是特别rational(理性)。但这也是有价值的——可能有人会做这种事。
这类东西很难和ChatGPT比强弱,它们是不同应用,有不同价值。
也可能出现一个由Agent组成的社会。
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有价值?不是因为他们的数学或编码能力强,而是因为他们拥有别人没有的信息。
中间商本质是拥有信息差。拥有信息差的人会想维护自己的权利和资源。这样的人会发明出更Multi-Agent(多智能体)或更 Distributed Network(分布式网络)。
在交易世界里,信息很重要,每个人只拥有信息的一小部分,这种情况会出现新的不同形态。可能是Multi-Agent,每个人有自己的Agent,Agent之间可以与百万甚至更多人交换信息,达成交易或某些目的。
根本上,现在非常强的巨头和重要节点,有动力继续推动中心化。但在中心化之外的力量,也有动力做一些非中心化的事情。
这个世界可能不会是单方压倒另一方,双方都会有自己的力量。
而这个世界智能的边界、研究的边界,可能不是由一家机构定义,而是由不同Super App共同定义的。
09 环境是记忆层级中最外层的部分
“这很哲学”
李广密:更关键的是,大模型技术没有垄断性。硅谷头3-4家好像都能追到一定的水平。如果OpenAI有垄断性,那是比较可怕的。
姚顺雨:我觉得暂时没有垄断性。但如果你能找到一个产品形态,把研究优势转换成商业优势,就会产生壁垒。
现在对于ChatGPT比较重要的是Memory(记忆)。
这是可能产生壁垒的地方。如果没有Memory,大家拼谁的模型更强。但有了Memory,拼的不仅是谁的模型更强,而是用户用哪个更多、哪个粘性更强。
我积累了更多Context,它能给我更好体验,我就会有粘性——这或许是研究优势转化成商业优势的方式。
张小珺:最近ChatGPT会出现灰色提示词,显示“记忆已更新”,这个更新的是什么?
姚顺雨:我最近没怎么用这个功能,但好像做了一些提升。
我怀疑是它产生或者使用记忆的方式变得更好。包括能更有效从很多用户对话中提炼出来,或者retrieve(检索)出更相关的内容。细节我不特别了解。
李广密:MCP(模型上下文协议)本质也是Memory吗?因为我的很多Context在我的个人软件、企业软件里,MCP本质也是hack(利用)Context的一种方法。
姚顺雨:某种程度上,是的。从Agent角度看,这个世界有一个Memory Hierarchy(记忆层级)。Memory Hierarchy最外层永远是环境。
有点像你考虑电脑,它有个Memory Hierarchy,从CPU缓存到内存再到硬盘,但最外层的Memory永远是外部环境。比如我插一个U盘、拔一个U盘,或者把东西上传到互联网,或者做个音乐变成光盘。
前年冬天,我读到冯诺依曼临终前写的一本书,The Computer and the Brain。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:Essentially, the Environment is always the most outer part of the Memory Hierarchy.(基本上,环境永远是记忆层级中最外层的部分。)
这很哲学。
对于人,你有你的Memory Hierarchy,有Working Memory(工作记忆)、Long-Term Memory(长期记忆)在脑子里,但最外层是你的笔记本、Google Doc、Notion,这些是你最外层Memory Hierarchy的一部分。
李广密:Long Context跟Long-Term Memory是什么样的关系?
姚顺雨:Long Context是实现Long-Term Memory的一种方式。
如果你能实现1亿或1千亿或无限长的Context,它是实现Long-Term Memory的一种方式。它是一种和人区别很大的方式,但这是有可能的。当然会有很多不同方式,不好说哪种是最好,或者最合适。
李广密:现在业界实现Long Context有Linear(线性)方式、Sparse(稀疏)方式,或者 Hybrid(混合)方式,你有倾向吗?
姚顺雨:我不想对方法进行评论,但我想对evaluation(评估)和task(任务)进行评论。
起码到去年为止,大家主要还在做所谓Long Range Arena(长距离评估基准),比如hay in the stack——我有一个很长的输入,我在中间插入一句话,比如 “姚顺雨现在在OpenAI”,然后我问你相关问题。
这是一个必要但不充分的任务。你能完成这个任务,是Not Memory Work(非长期记忆任务)中的前置条件,但远不是充分条件。它是必要条件,但现在大家有点陷在这个必要条件,没有创造更难或更有价值的任务,这是个问题。
当没有一个很好的评估方式,很难真正讨论各种方法的好坏。
10 Chatbot系统会演化成Agent系统
“人和Agent交互的方式是什么样?”
张小珺:对于未来12到24个月,Agent领域有可能发生的事情,你有哪些预测?
姚顺雨:首先,这些模型公司的Chatbot系统会演化成一个很自然的Agent系统,它是一个很自然的过渡。
Grok、ChatGPT或Anthropic Cloud,默认的交互方式会是Agentic(智能体式的)交互方式。Chat可能还会保留或作为一个子集,但Agent会成为一个很显然、更重要的交互方式。
会有新的类似Cursor的产品出现,Cursor是在coding和IDE(集成开发环境)环境下做的Copilot(辅助编程助手),但我觉得会有机会做一些新的环境或更大环境下的Copilot。
这两种大的交互方式是互补的,或者说不一样的正交的。
一边是,我有一个基于模型的,可能是一个remote(远程)的Virtual Machine(虚拟机)或者Environment(环境),我在里面做很多事;另一边是,有很多既有的环境,比如既有的软件,或者既有的场景,我把Agent或AI能力引进去。
大趋势可能是,两方面都会往下发展。
李广密:如果我们想推动Agentic能力变得更强,要在哪里做工作?是在Pre-Training做工作还是在RL做工作?如果我是一个应用创业者,这两个东西是做不了的,最多尝试一些端到端RL的过程,对吧?
姚顺雨:最重要的还是想清楚价值,你应用的价值是什么,痛点是什么,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?
虽然你不能做Pre-Training,但更有价值的是:Agent和数字世界的交互环境是什么样的?(是基于MCP还是API,还是别的东西?)人和Agent交互的方式是什么样的?
这两个是你可以去做的,并且它需要很多设计、很多基础设施、很多工程,需要各种各样的东西。现在还远远不够好,有很多进步空间。
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是:怎么构建一个生态系统,或者怎么积累用户的Context(上下文)或Intention(意图)?这还有很多可以做的空间。
李广密:你刚才提到Agent Infra(智能体基础设施),如果两年后Agent已经大爆发,巨量的Agents在数字世界运行,需要重新帮Agents设计一套新的数字化系统吗?
Agent需要的虚拟机、电脑、浏览器、搜索的API、身份认证、经济系统等等,这套Infra是为Agent设计的,而不是完全为人设计的?
姚顺雨:我个人感觉两年以内,这个世界还不会变得这么分布式,还是更偏中心化。就是说,会有一些Super App。
当然现在有很多创业公司,但做得好的就是那么几家。两年内还是会有些Super App,这些Super App会有各自的Infra,有各自的Environment或交互方式。
两个事情都可以做到极致,就是一个是基于用户local(本地)的Digital Environment(数字环境),比如我有个手机,有个电脑,有个软件,我已经在这了,我怎么把它去扩充,怎么把它变得更好?
另一个是从头创造新的Environment,比如我做Deep Research或我做Operator(操作者),我实际上创造一个新的Environment。这两个事都还有很多可做的空间。
张小珺:两年后呢?
姚顺雨:这个世界变化很大。有些像科幻的预测、想法或图景。没有人可以预测两年后发生什么。
张小珺:在你看来,大型科技公司是否应该重新开启Pre-Training叙事?(自己从头探索Pre-Training)
姚顺雨:这里面涉及cost和value取舍。现在做的人很少,是因为成本非常大,但带来的additional value(额外价值)没有那么大。
即使你做完Pre-Training,你还需要做Post-Training、RLHF(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,Reinforcement Learning with Human Feedback)等一系列工作,才能真正把模型价值释放出来。
但如果有一天,这个世界上存在很多不同的Super App、不同的交互,它们需要不完全相同的模型能力,甚至需要不同的模型,这些差异的价值足够大,能够证明Pre-Training的成本是合理的,那么Pre-Training就是合理的。这最终是value和cost权衡问题。
李广密:Pre-Training和RL未来的关系会是怎样的?会不会更多先验知识被放到Pre-Training里?
姚顺雨:我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是:不同应用需要不同形态的Agent,构造方式可能不一样。
如果我只需要下围棋,我直接做AlphaGo就可以了,不需要Pre-Training,也不需要其他。
如果我有一个非常垂直的场景,这个场景价值足够大,我又有很多数据,可以形成闭环,我也许基于一个主要由RL驱动的系统就能work。
像Google的广告系统或TikTok的推荐系统,有点类似这样的系统——我找到了一个足够封闭的环境,做类似RL的事,就可以带来足够多价值,那这个路径是合理的。
但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长尾任务,它们需要泛化,需要构建一个更像人的系统。你虽然不是无所不知,但你可以学习,你可以通过在线学习进入一个新的公司、适应环境、完成新的任务。在这些地方,Pre-Training重要性会更高,因为它带来更强的泛化性。
所以不同应用会有不同技术路线。但技术路线毕竟是工具,只要你的value大于cost,技术上的选择是flexible(灵活)的。
没有哪种技术路线一定会胜出。只要它在经济上成立,就有可能性。
第四章 人类的全局
11 人与系统
Agent要不要像人?
“是一个效用问题”
张小珺:在你研究Agent的过程中,对于人,你有更深的认知吗?怎么看人和Agent的同与不同?
姚顺雨:我意识到,人之所以能泛化,是因为人能推理。
这个很有意思。我2018年在MIT Josh Tenenbaum实验室——他是一个认知科学的大佬——我学了很多认知科学的东西。
认知科学,或者计算认知科学,一个核心故事是:我们现在的AI虽然有很多进展,但还有很多问题。我们应该去看看,人有哪些优势,人是怎么做这些事情的,为什么人能把这些事做得更好?比如说,人能够从几个样本中泛化,但机器做不到,为什么?我们要从人身上去寻找这些方法,再把它应用到AI上。
后来我的认知有了变化。我发现,现在真正能奏效的AI系统,跟人还是很不一样。比如Scaling Law、强化学习,还有很多训练策略,它们和人类学习的方法本质是不同的。
我现在觉得,一个更好的方法是:你先去思考人能做什么,而机器现在不能做。这是客观事实。
但你找到差异之后,你可以基于第一性原理去思考,如何解决这个问题。你不一定要依赖“人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”来解决它。
比如说,人现在能做的事情是什么?我可以进一家公司,在里面工作7天,我能积累公司的Context。即使我不是很聪明,但我依然能完成很多AI做不了的事。这个差异客观存在。那怎么解决?
可能认知科学或神经科学会告诉你:人脑有海马体(Hippocampus),有情节记忆(Episodic Memory),有某种架构或机制。但我觉得,我们不需要完全照搬生物机制。可以从第一性原理出发,设计Long-Term Memory该怎么做。
所以,从人身上可以借鉴的一点:哪些事情是人可以做,而机器目前不能做?这点比较robust(稳固)和客观。但至于“人是怎么做到的”,以及“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要借鉴这种方式”,这个问题本身更主观、也更 noisy(带噪声)。
神经科学或认知科学也没有100%解答这些问题,只提供了猜想或理论模型。另外,即便被证实,比如人类视觉是目前研究比较透彻的领域之一,人类大脑有六层皮层(cortex),每一层有各种结构和功能。但从这里获得的启发是:我们也许要构建新的神经网络,而不需要照抄那些细节。
张小珺:比方说,设计Agent在什么情况下,需要它越来越像人?什么情况下需要它不像人?
姚顺雨:Again,这是一个Utility Problem(效用问题)。
很多问题上,人的方式并不一定更有价值。比如下围棋、开车。我不知道。大多数人可能开车的方法并不好,也许基于规则有更好的开车方式。但有些事情,人就是做得更好。那你就应该思考,怎么去bridge the gap(弥合这个差距)?
下围棋、打游戏,基于强化学习可以学到和人不一样、甚至更好的方式,就不需要像人。
但如果在一个公司打工,和老板搞好关系,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,人就是比AI做得更好,就需要更像人。
张小珺:你怎么思考人和Agents未来的关系?
姚顺雨:这是一个交互方式的问题。
很有可能有很多Agents,长得并不像人,和它交互的方式并不像人——可能是平台、页面、游戏,或者别的东西。你就不会把它拟人化。当然,肯定会有很多拟人化的Agent。
李广密:如果Agent有了长期记忆,它是不是就是你的朋友了?如果它是你的朋友,人和Agent就平等了,是不是我们就要给它发身份证了?
姚顺雨:发身份证的目的是什么?
李广密:它作为独立个体跟我们共存。
姚顺雨:会有可能吧。这些事情最终还是从Utility(效用)出发。
一个事情如果有价值,就会产生。比如,很多人很孤独,他需要一个朋友,技术如果能创造这样的体验,拟人化就是合理存在的未来。
但如果它去做一个平台、一个推荐、一个游戏,这个技术会有很多不同的交互方式,让你感觉它不像一个人,或者你根本感觉不到有区别。你就不会把它看成拟人化。
还是会基于这个事情的经济价值。
李广密:你提到经济价值。你觉得AI Agent跟Crypto(加密技术)未来有结合的地方吗?
比如,Crypto这一套智能合约机制,如果跟Agent结合,在未来有没有可能是这样:一个Agent帮我完成某个任务,这个任务有一个公允价值计量。任务完成之后,就可以按照智能合约的约定去分配经济利益。
这样是有机会探索出一种叫做value-based(基于价值的)商业模式。只是说,现在我们还不太能准确衡量这个任务的客观供给价值是多少。
姚顺雨:我对Crypto了解不多,但可能一个核心问题是:这个技术的演变,会变得更中心化还是去中心化?——两边都有argument(论点)。
中心化论点是:现在这种新的超级公司,OpenAI或Anthropic,它们有可能变成one trillion、ten trillion、hundred trillion(万亿、十万亿、百亿万亿)级别的公司。它们可能会占据绝大多数资源,尤其是算力,也有能力去创造出一个Super App或Super Platform(超级平台),拥有巨大中心化优势。
而去中心化argument(论点)是:每一个个体都可以被赋能。现在人和人之间之所以差距这么大,是因为存在信息差、认知差、智能差。如果智能变得便宜,像电一样,它也可以赋能给大多数人。
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。
我最近的一个思考是这样:我感觉人类社会是一个网络,它有两个重要性质:
过去几百年发生的事情是这样:网络越来越中心化,贫富差距越来越大,二八定律、马太效应更明显;但与此同时,平民或普通人翻身的机会也变多了。
如果是在古代,门阀制度、九品中正制,或者欧洲贵族制度,农民永远是农民。印度种姓制度也一样,有明显的阶级固化。
看起来,技术发展的趋势是两件事同时加剧——一方面,中心化加剧,因为效率这个因素是根本性的;另一方面,创造新东西的机会,起码到目前为止,是越来越多的。
变得更中心化和变得更diverse(多样化),可能并不矛盾。
但未来是不是一定会持续下去,也不好说。
12 OpenAI的抉择时刻
“如果你没有different bet,
很难超越前面的霸主”
张小珺:我想聊聊OpenAI。我记得你提到OpenAI的几次尝试很有意思。
它最初的计划是构建Gym,一个用于各种游戏的标准强化学习环境。后来是World of Bits和Universe项目,试图把整个互联网或计算机交互编程成一个游戏。一旦能把整个数字世界变成一个环境,用聪明的强化学习算法解决它,就拥有了AGI。
但这套思路并没有奏效。直到GPT-2和GPT-3出现,人们才意识到,之前缺失的是先验知识。你需要一个强大的语言预训练过程,把一般常识和语言知识提炼进模型中。再通过微调,让它成为一个能浏览网页的或能对话的智能体。
你能不能更详细讲讲,OpenAI探索过程背后的思路演化?从Gym到Universe到GPT这一整条路径的尝试中,转折点是怎么发生的?
姚顺雨:这是我自己的总结和揣测。
OpenAI是一个比较bottom-up(自下而上)的公司。在最初7、8年里,它更像是一个research lab(研究实验室),每个人有各种各样的想法,做各种各样的尝试。可能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。
但客观看,一开始大家的重点还是聚焦强化学习,当时最火的方向是这个,对吧?
DeepMind大概2015年刚成立,那时AI领域最受关注的公司是DeepMind,它最成功的成果也是强化学习。GPT出现前,最成功的AI项目是AlphaGo。很自然,OpenAI也做强化学习。
但问题在于,如果你没有一个different bet(不同的下注方向),很难超越前面的霸主。如果OpenAI一直做强化学习,可能很难超过DeepMind。即使你在某些任务上做得比它好,人们提到强化学习,想到的还是DeepMind。
你要想超越之前的霸主,就必须有一个different bet。而GPT是那个不同的赌注——但这个选择在当时是一个非共识的事情。
我可以讲个例子:我导师是GPT‑1第二作者,他在OpenAI待了一年,然后去普林斯顿当教授。他对这件事是有点怀疑的。
他觉得GPT‑1的结果也不是特别好,在排行榜上也不是分数最高,而且训练花了很多算力。当时已经有Scaling Law初步雏形。2017年,Ilya就跟我导师说:”Language is basically solved, and we just need to scale up." 语言模型的问题已经被解决了,现在只需要扩展规模就行了。
但即使你在OpenAI,即使你是GPT作者,你也可能没有形成共识。所以OpenAI当时做的是一个非常反共识的决定。现在已经变成了共识。但接下来,你还需要寻找下一个反共识的方向。
张小珺:当时其他人对你导师的看法是怎样的?
姚顺雨:我说实话,当时OpenAI内部绝大多数人也不认为scale-up(扩大模型规模)是最promising(有前景)的方向,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。
Ilya最大贡献并不是他做了GPT‑1,或者他具体参与了什么技术工作;而是,他是那个号召大家all in(全力投入)这个方向的人。
Dario(Anthropic联合创始人兼 CEO,曾是OpenAI研究副总裁)也是。他最大贡献不是提出某个具体技术,而是:作为一个创始人,我敢赌。我敢赌这个方向,把所有钱砸进去。
李广密:有人愿意去做GPT‑3是特别关键的。像Dario也好,Tom Brown(Anthropic联合创始人)也好,他们敢于把GPT‑3做出来,这件事让人看到了更大希望,也泛化了。
姚顺雨:对,当然好处在于,你并不需要所有人达成共识。只需要有足够多人达成共识,就可以把它做出来。
张小珺:对于OpenAI内部来说,强化学习在什么时候开始变得特别重要?
姚顺雨:强化学习一直很重要。即使我在做GPT的时候,John Schulman(OpenAI联合创始人之一,强化学习领军人物)还是在继续做强化学习。并不是我做了GPT就把强化学习扔掉了。而是公司70%、80%的资源在做强化学习,一些别的东西还在做。
后来证明,ChatGPT成功,强化学习也很关键。没有RLHF,没有Alignment(对齐)技术,它也没办法形成一个产品。
历史并不是说我把强化学习彻底抛弃,转而走另一条路,再返回来走强化学习,而是更soft(柔和)的过程。
李广密:接下来几年,你预计会有更多GPT‑3时刻吗?
姚顺雨:会有新的scaling dimension(扩展维度)出现。如果你有大量的Memory(记忆),你的test-time compute(测试时计算资源)就会有所增加,可以用新的方式scale(扩展)。
如果你有了Multi-Agent(多智能体系统),那你的test-time compute又会出现另一个新维度去扩展。
我觉得会有新的scale dimension出现,但当你有很多scale dimension,怎么去选择?怎么基于某一个应用去分配不同scale维度的比重?——这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。
13 假若你是一个CEO
“首先我肯定会学习”
李广密:顺雨,如果你是一个全球超大互联网或科技公司的CEO,今天这个公司还没有自己的模型,没有好的研究文化,甚至没有好的AI战略,你作为CEO会怎么做?
姚顺雨:首先,我肯定会学习,我会想弄清楚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。如果你作为CEO不懂这个事情,所有事情会变得很难。
很多时候,一个公司的bottleneck(瓶颈)就在于,CEO 对这个事理解不够。如果你不理解,去招一些很好的人、做一些事情,你很可能被他们忽悠。所以,首先要自己学习。
然后要从创造新的价值来思考问题。毕竟你不是技术专家,而是一个CEO,你有一些场景、一些资源、一些优势。从第一性原理看,一个新的技术产生了,你要思考的是,怎么用这些新技术结合你现在的资源去创造新的价值。
当然,你可以尝试做一个和当前业务完全不一样、但价值非常大的事情,比如ChatGPT,但对大多数公司来说,即使很有钱、很强,也不一定make sense(合理)。
所以,第一是自己要学习技术;第二是要思考怎么创造新的价值。
李广密:如果你成为了伯克希尔的CEO,未来要拿出500亿美金allocate(分配)到AGI行业,你会怎么allocate这笔钱?——既能体现回报,也能体现对人类的贡献。
姚顺雨:这是个很好的问题。取决于你有多少精力,或者有多少资源分配颗粒度。
当然现在OpenAI、Anthropic,这些模型层公司,大概率会有更大价值。
还有一类很有价值的,是能积累User Context(用户上下文),或者能构建特殊Environment(环境)的公司。最终如果AI或AGI是一个系统,它需要有Intelligence(智能),需要有Environment,还需要有User Context,或者对用户的理解。
现在有很多User Data(用户数据)或User Context 的公司,有点像发明车之前的煤炭、煤矿,或者像发明汽车之前的石油公司。
从这个角度,微信或大平台,还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好平台,它积攒大量的Context。
如果Intelligence是一个可以逐渐民主化、逐渐变得便宜、逐渐普及,拥有这样的平台,拥有这样的Environment,拥有这样的Context,可能会是一个很强的壁垒。它可能还是一个很好的投资。
李广密:如果你是Cursor的CEO,你会去做Pre-Training的事情吗?
姚顺雨:我肯定会训练模型,或者尝试训练模型,但做不做Pre-Training看情况。
Coding是非常主线的任务,所有大厂都会把模型的coding做好。所有的Pre-Training、Post-Training、RL,都会考虑到这一点。
这个情况下,要不要做可能取决于,首先这些闭源模型做得有多好,其次开源模型做得有多好,中间有多少gap,你能填补多少这样的gap。
但当然,如果你有很多钱,有很多资源,想把这事情做了,也是合理的。
张小珺:今天顺雨当了很多公司的CEO,那我再问一个:如果你是微信的一号位,你会怎么在微信里做Agent?
姚顺雨:我可能会不急,先观望观望。
我好像没有理由要急。我会观察,我会学习 AI,会观察有没有什么新的交互方式很有意思。但我不会急着去做很多事——我有易守难攻的地方,为什么要急着进攻?
比较危险的是一个颠覆性的创新。真正的危险,不是说一个类似于微信的东西打败了微信,而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东西打败了微信。
就像微信打败了QQ。当时担心的并不是一个类似QQ的东西打败了QQ,而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产品去打败这个东西。需要对颠覆性创新有所警惕。
但如果是这些incremental(渐进式的)创新,这种小的创新,早做晚做可能区别没有那么大,也不用太担心。
李广密:所有人都说微信卡位好,但今天微信还没有很激进地投入,如果未来Multi-Agents 、Long-Term Memory这些问题解决了,但这个Agent系统不长在微信上,是比较恐怖的。原有网络不一定有价值。
姚顺雨:这取决于人类的网络会变成什么样?你会有更多Agent朋友,还是更多人类朋友?或者你有更多Agent职业上的交互,还是有更多人类职业上的交互?
微信上你既有朋友,也有基于职业的交互——比如我要买个东西,我要咨询律师,对吧?
这取决于人类的网络会变成什么样。但总会有一个这样的网络,基于这个网络,肯定会需要有基础设施,需要有平台。
李广密:怎么保证AGI实现之后的安全问题?微信过去还是一个比较负责任、比较安全的平台,那如果未来power(能力)很强了,很多坏人来做坏事,甚至颠覆人类,安全问题长期怎么解决?要有AI宪法吗?
姚顺雨:安全是很复杂的问题。比如ChatGPT,如果它不安全,产品就失败了,没有商业价值。即使是为了商业价值,它也会重视安全。
但现在的主要分歧是,需不需要产品之外、更意识形态上的安全?这个大家没有定义清楚。
前者容易解决:如果你有一个好的应用,你总会有办法解决安全问题,我相信。至于第二者,会有很大不确定性,我很难评价。
李广密:你个人会担心AGI实现之后的安全问题吗?
姚顺雨:我会担心。但现在最大问题是——AGI还没实现,我们还没创造足够价值。
如果我们还没想清楚,怎么把它变得有价值,就急着把它变得很安全,好像没有意义。
14 这个时代,做上限更高的事更好
“如果敢想、胆子大,就会有好事发生”
张小珺:你作为AI研究者,博士期间工作已经获得了很多关注,在你眼中,你做对了什么?
姚顺雨:我想做的就两条线:简单通用的方法、有实际价值的任务。这些任务往往是,如何在真实数字世界创造新的价值。这是一个处女地,是一个巨大的宝藏。我恰好挖掘了一些东西。
需要你想得足够大胆或足够通用吧。
另一个很重要的是:要去看很多东西的交界处。ReAct之所以能做出来,因为我们选了一些自然语言处理的任务,也选了一些游戏的任务,需要把自然语言处理和强化学习的边界打通。但很多人会陷入一个学科内部,就更难去做更通用的东西。
张小珺:ReAct在做的过程中有遇到什么坎吗?
姚顺雨:最难的都是找任务。
大多数好的方法提出,是因为它有一个特定任务,这个特定任务恰好激发出一个通用方法。比如PPO(Proximal Policy Optimization,一种强化学习优化算法)一开始是为了解决一个特定问题;Transformer一开始是为了解决一个特定任务;Attention(注意力机制)受翻译这个任务影响很深。
但我的经历比较特殊,很多时候我是脑子里先想到一个东西,我觉得它很通用、很好。但我要去找一些任务,证明它很通用、很好,或者未来有价值。它现在还没有足够多价值,但你需要先找一些简单任务去证明它有价值。这是很难的。
创业需要product market fit,做research需要method-task fit(方法和任务的匹配)——这是最难的。
张小珺:你曾经想到最激进的一个任务是怎样的?
姚顺雨:这个时代再激进也不叫激进——Anything is possible。
毕业前我想得多的是,怎么创造一个爱因斯坦?我那时是比较academia(学院派)的人——你在普林斯顿,你的偶像是冯诺依曼、爱因斯坦——很自然,能想到最有意思的任务是,我能不能发现下一个相对论?这毫无疑问能标志,AGI或ASI(超人工智能)实现了。
后来,我到了硅谷,到了加州,进入公司之后,我发现人类的组织也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情。如果能创造一家新的公司,创造一个one trillion dollar(一万亿美元)、基于Agent的公司,是很有意思的。
张小珺:为什么是人类的组织也很有意思,而不是人类的产品很有意思?
姚顺雨:产品当然很有意思,但很多组织的方式,就像一个general method(通用方法),能创造很多不一样的伟大的东西。比如股份制、组织架构,它就像非常通用的AI方法一样,创造了很多不一样的伟大的东西。
张小珺:在你的成长路上,你的mindset(思维方式)跟同龄人差不多吗?还是不一样?
姚顺雨:我的路径挺按部就班的,也没有跳级,没有做什么很surprising(让人惊讶)的事情。但我对一个东西的价值,或者taste(品味),有自己的看法。大家往往会倾向于做一个确定性比较高的事情,包括做研究、做公司。
但我觉得恰好是这个时代,你去做上限更高的事情是更好的。
因为现在有一个巨大的机会。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巨大的机会,最佳路径可能是去做incremental(渐进式)、确定性强的事情,一步一步地积累。但恰好有一个上限非常高的事情。
如果你敢想,或者你胆子特别大,或者你想象力很丰富,就会有好事发生。
张小珺:在你成长路上,对你启发大的是什么?是书、电影、音乐?哪些东西塑造了你的mindset?
姚顺雨:看书挺有帮助,我是一个喜欢看杂书的人。什么书都看,什么电影都看,什么地方都想去。
我从小是一个比较general的人——我想试图变得很通用,试图了解很多不同的学科,做很多不同的事情。
但后来我发现,一个人即使再聪明、再有精力,他能理解的知识或能做的事情,也只是人类社会积累的知识的很小一部分。更好的是,你去创造一个比你更通用、更general的事情。
我好像一直对于通用性,有一种执念或追求。
张小珺:通用性意味着什么呢?——可以足够简洁?
姚顺雨:我不知道,但我从小就是想学习很多不同学科,都很有意思。
我在姚班很多同学,他们是那种很deep(深度的)、很focus(专注的)同学——我去做竞赛,我就把这个事做到极致,不停刷题,做到世界金牌。
但我好像不是那种性格,我是那种——我会看很多数学,也会看很多历史,会看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东西。
张小珺:你会刷竞赛吗?
姚顺雨:我也搞竞赛,但没有本科同学那么厉害。我是信息学拿了全国银牌。
张小珺:你是清华的说唱社联合创始人,对吧?我昨天去翻了一下你的网易云音乐。
姚顺雨:被你找到了?看来你有Deep Research的能力。
张小珺:你最喜欢的说唱歌手是谁?
姚顺雨:我有很多喜欢的说唱歌手。说唱很有意思,每个人风格都很不一样,这点是很多人喜欢说唱的原因——你有自己的个性、自己的flow(节奏)、自己对生活的思考,你可以创造不一样的东西。它不一定是最好的,但大家是不一样的,这点很吸引人。
张小珺:它跟你做AI有相似之处吗?
姚顺雨:GPT-3刚出来,大家都觉得很厉害嘛,我想到第一个做的就是,看看能不能生成说唱歌词,并且有内容性。似乎今天还是很难。也许说唱歌手是一个被人们低估的工作。
张小珺:填词,这不就是predict next token(预测下一个词元)在做的事情吗?
姚顺雨:一个东西好听、flow好、听上去舒服,是很难被量化的reward。很多时候一个东西,比如flow或style,它出现太多了,就不好了。独特反而是好的。真正伟大的说唱歌手,有很多独特的对生活的思考,而AI还没有生活。
张小珺:有可能有对于智能来说,比语言更本质的存在吗?
姚顺雨:在特定领域,肯定有比语言更好的表示,比如围棋。
但语言的诞生,不是为了处理某个特定任务的效率或交流,它为的是打通所有任务或者打通人的认知能力,形成一个通用的表示。
它并不是为了某个特定任务最优而优化,它在特定任务上有冗余性,但它整体是通用的。
AI当然也可以创造一个新的语言,可能效率更高。但我觉得,最终大概率就是英语。因为人类已经有很强的先验知识,而且人有这样的价值取向或动机,想让机器的语言和人更像。
这样,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它、控制它、监控它、改变它、操控它,似乎是个很自然的选择。
张小珺:你内心的驱动力是什么?你的愿景是什么?你10年后想成为谁?
姚顺雨:用一个非常俗的话说,希望你对这个世界创造一些不同——探索新的、根本性的研究,是一种创造不同的方式;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的产品形态,也是一种创造不同的方式。
如果我现在去做一家类似xAI或Thinking Machine的公司,或者做一个类似Chatbot或Assistant的产品,还是可能赚很多钱,商业上很成功;但如果我做了一个形态很不一样的东西,失败了——我起码探索了不一样东西,会更有意思吧?
我导师令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句话。学术圈经常发生这样的事——你有一个想法,然后别人做了,你会很烦。他说:If someone else can do it, then it's okay to let them do it(如果别人能做,那就让他们去做吧)。
从人类全局的角度,如果这个事情很多人能做,别人做可能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区别?对这个社会,或者对整体来说,似乎没有什么变化。
当然,有人说这个非常假。最终你会发现,这个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替代的。相对论即使没有被提出,也会有人提出,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不在,另一个人不能提出了——但是,我觉得这话还是有道理的。
如果你很清楚看到别人就在做这个事,你可以选择去和他卷。如果你要和他卷,你更有效率,或者你能做得更好,也是合理的。或者,你也可以去做一些不一样的探索。
我觉得,最终你要对这个社会产生价值。
但这个时代很幸运的一点:这个技术非常通用,这个技术非常伟大,有足够多探索的空间。
另一点是,我想让生活更有趣,更有意思,更快乐,就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。这很难用语言解释,就是一个taste(品味)或preference(偏好)的问题。
张小珺:你会考虑创业吗?
姚顺雨:OpenAI大多数人都会考虑创业。现在是非常exciting的时候。已经有很多OpenAI的人出去创业了。我需要去做更有挑战的事情,很自然会去创业。
但还是应该找到一个好的事情。我喜欢把事情想得清楚一点再去做。
张小珺:我们最后还有几个快问快答。
姚顺雨:好。
张小珺:一个全球范围内你喜欢的食物。
姚顺雨:我喜欢椰子。
张小珺:一个全球范围内你喜欢的地点。
姚顺雨:我很喜欢伊斯坦布尔。
张小珺:一个少有人知道但是必须知道的知识点。
姚顺雨:我挺建议大家去看《智能简史》这本书。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知识点。
为什么大多数动物都是左右两侧对称,并且有一个像嘴一样的食物入口,有一个像肛门一样的食物出口?为什么气体是同一个口,而食物和水是两个口?这个很有意思,有些本质原因。
张小珺:什么本质原因?
姚顺雨:你会发现,如果你要做navigation(导航),在这个世界中移动,左右对称的结构最优。世界上所有交通工具都是左右对称的。因为你可以一个方向前进后退,另一个方向向左转向右转。它和车和飞机都是左右对称,结构是类似的。
至于食物和气体还有别的原因。
张小珺:基于你所有读过的书,推荐两本必读书。
姚顺雨:《智能简史》这本书很有意思,是我去年读的。
我会推荐各种各样的自传。传记很有意思,好像你在体验别人的生活。
张小珺:你心目中影响 AI 进程的几篇论文。
姚顺雨:有很多,我觉得没有最重要——Backprop(反向传播)、Transformer(变换器)、GPT(生成式预训练变换模型)——都是积累的过程,没有一个是最伟大的工作。
李广密:你会对Agent创业者有什么建议吗?
姚顺雨:可能有点老套:想清楚你的价值是什么。技术是工具,理解技术趋势很重要,但创造价值是最重要的——想清楚你为用户带来了什么样的增量价值,这是最主要的。
张小珺:基于你当下的认知,一个最关键的重要的bet是什么?
姚顺雨:就是bet on有different Super App(不同的超级应用)的产品形态,有不同的交互方式。
如果你不相信这一点,世界就变得很灰暗,就是只有OpenAI或者Anthropic有机会。
但如果你相信这一点,就会有很多新的机会。
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 “ 语言即世界Ianguage is world “,作者 张小珺
【开源免费】OWL是一个完全开源免费的通用智能体项目。它可以远程开Ubuntu容器、自动挂载数据、做规划、执行任务,堪称「云端超级打工人」而且做到了开源界GAIA性能天花板,达到了57.7%,超越Huggingface 提出的Open Deep Research 55.15%的表现。
项目地址:GitHub:https://github.com/camel-ai/owl
【开源免费】Browser-use 是一个用户AI代理直接可以控制浏览器的工具。它能够让AI 自动执行浏览器中的各种任务,如比较价格、添加购物车、回复各种社交媒体等。
项目地址:https://github.com/browser-use/browser-use
【开源免费】字节工作流产品扣子两大核心业务:Coze Studio(扣子开发平台)和 Coze Loop(扣子罗盘)全面开源,而且采用的是 Apache 2.0 许可证,支持商用!
项目地址:https://github.com/coze-dev/coze-studio
【开源免费】n8n是一个可以自定义工作流的AI项目,它提供了200个工作节点来帮助用户实现工作流的编排。
项目地址:https://github.com/n8n-io/n8n
在线使用:https://n8n.io/(付费)
【开源免费】DB-GPT是一个AI原生数据应用开发框架,它提供开发多模型管理(SMMF)、Text2SQL效果优化、RAG框架以及优化、Multi-Agents框架协作、AWEL(智能体工作流编排)等多种技术能力,让围绕数据库构建大模型应用更简单、更方便。
项目地址:https://github.com/eosphoros-ai/DB-GPT?tab=readme-ov-file
【开源免费】VectorVein是一个不需要任何编程基础,任何人都能用的AI工作流编辑工具。你可以将复杂的工作分解成多个步骤,并通过VectorVein固定并让AI依次完成。VectorVein是字节coze的平替产品。
项目地址:https://github.com/AndersonBY/vector-vein?tab=readme-ov-file
在线使用:https://vectorvein.ai/(付费)
【开源免费】DeepBI是一款AI原生的数据分析平台。DeepBI充分利用大语言模型的能力来探索、查询、可视化和共享来自任何数据源的数据。用户可以使用DeepBI洞察数据并做出数据驱动的决策。
项目地址:https://github.com/DeepInsight-AI/DeepBI?tab=readme-ov-file
本地安装:https://www.deepbi.com/
【开源免费】airda(Air Data Agent)是面向数据分析的AI智能体,能够理解数据开发和数据分析需求、根据用户需要让数据可视化。
项目地址:https://github.com/hitsz-ids/airda
【开源免费】AutoGPT是一个允许用户创建和运行智能体的(AI Agents)项目。用户创建的智能体能够自动执行各种任务,从而让AI有步骤的去解决实际问题。
项目地址:https://github.com/Significant-Gravitas/AutoGPT
【开源免费】MetaGPT是一个“软件开发公司”的智能体项目,只需要输入一句话的老板需求,MetaGPT即可输出用户故事 / 竞品分析 / 需求 / 数据结构 / APIs / 文件等软件开发的相关内容。MetaGPT内置了各种AI角色,包括产品经理 / 架构师 / 项目经理 / 工程师,MetaGPT提供了一个精心调配的软件公司研发全过程的SOP。
项目地址:https://github.com/geekan/MetaGPT/blob/main/docs/README_CN.md
【开源免费】graphrag是微软推出的RAG项目,与传统的通过 RAG 方法使用向量相似性作为搜索技术不同,GraphRAG是使用知识图谱在推理复杂信息时大幅提高问答性能。
项目地址:https://github.com/microsoft/graphrag
【开源免费】Dify是最早一批实现RAG,Agent,模型管理等一站式AI开发的工具平台,并且项目方一直持续维护。其中在任务编排方面相对领先对手,可以帮助研发实现像字节扣子那样的功能。
项目地址:https://github.com/langgenius/dify
【开源免费】RAGFlow是和Dify类似的开源项目,该项目在大文件解析方面做的更出色,拓展编排方面相对弱一些。
项目地址:https://github.com/infiniflow/ragflow/tree/main
【开源免费】phidata是一个可以实现将数据转化成向量存储,并通过AI实现RAG功能的项目
项目地址:https://github.com/phidatahq/phidata
【开源免费】TaskingAI 是一个提供RAG,Agent,大模型管理等AI项目开发的工具平台,比LangChain更强大的中间件AI平台工具。
项目地址:https://github.com/TaskingAI/TaskingAI
【开源免费】MindSearch是一个模仿人类思考方式的AI搜索引擎框架,其性能可与 Perplexity和ChatGPT-Web相媲美。
项目地址:https://github.com/InternLM/MindSearch
在线使用:https://mindsearch.openxlab.org.cn/
【开源免费】Morphic是一个由AI驱动的搜索引擎。该项目开源免费,搜索结果包含文本,图片,视频等各种AI搜索所需要的必备功能。相对于其他开源AI搜索项目,测试搜索结果最好。
项目地址:https://github.com/miurla/morphic/tree/main
在线使用:https://www.morphic.sh/
【开源免费】XTuner 是一个高效、灵活、全能的轻量化大模型微调工具库。它帮助开发者提供一个简单易用的平台,可以对大语言模型(LLM)和多模态图文模型(VLM)进行预训练和轻量级微调。XTuner 支持多种微调算法,如 QLoRA、LoRA 和全量参数微调。
项目地址:https://github.com/InternLM/xtuner
【开源免费】LangGPT 是一个通过结构化和模板化的方法,编写高质量的AI提示词的开源项目。它可以让任何非专业的用户轻松创建高水平的提示词,进而高质量的帮助用户通过AI解决问题。
项目地址:https://github.com/langgptai/LangGPT/blob/main/README_zh.md
在线使用:https://kimi.moonshot.cn/kimiplus/conpg00t7lagbbsfqkq0